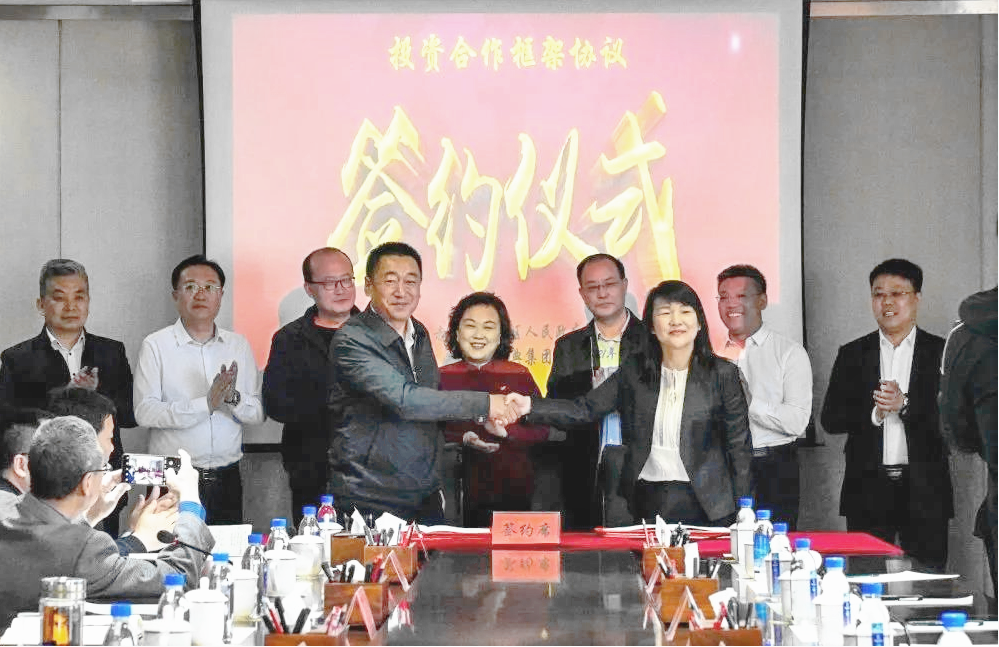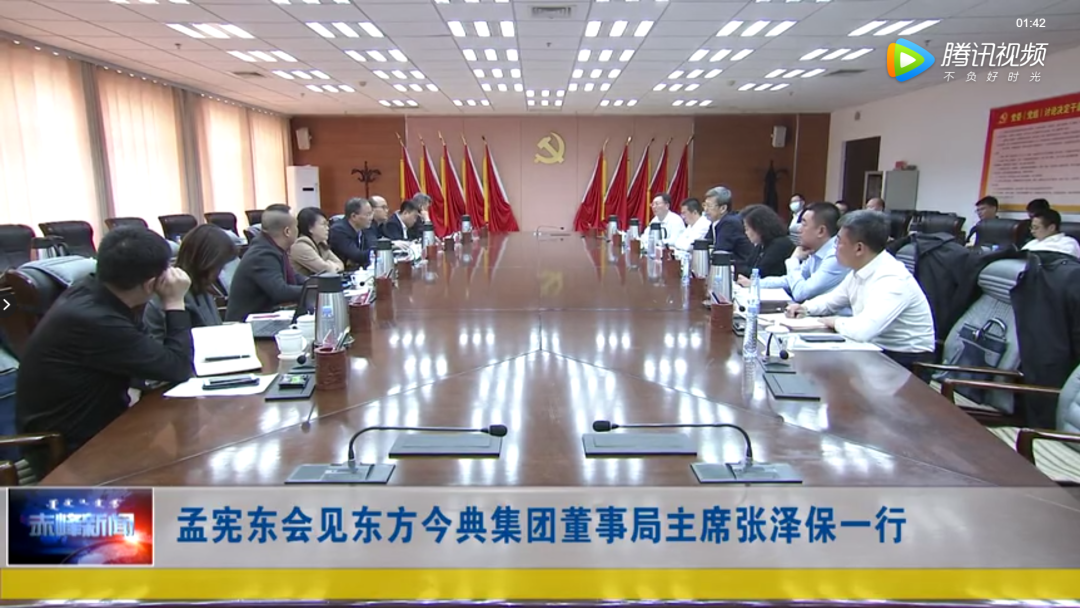您的位置:首页 >新闻 > 财经要闻 >
对增值税制与地区竞争制度的新领悟
为问题,都是因为中央政府打压房价,从而造成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不如当初借债用于征收土地、建设开发区时的预期,于是有可能出现收不抵支、无力偿还所有债务的违约风险——还有就是高速公路节假日免费政策也造成高速公路的建设成本回收年限拖长,但这个造成违约风险的可能性比较低,因为只是拖长了回本时间,不像卖地收入是一次性形成,如果收入不能覆盖所有成本,并不能通过拖长时间等待后续有收入慢慢覆盖。 当然,不是所有地方政府的项目都一定能获得不低于市场利率的回报率(即从机会成本的角度看达到了收支相抵),但这正如不是所有企业的生意都能成功一样,这只是个别地方政府的风险,属于非系统风险,只要通过竞争能淘汰失败者,这类非系统风险从来都不是中央政府需要担心的(正如个别企业做生意失败破产是非常正常的市场竞争的结果,不会造成经济危机,不需要政府担心)。需要担心的是系统风险,即遍及整个系统之内的主体都普遍失败,说明出问题的不是个别主体,而是整个系统本身有问题。如我在《南都》发表的文章所言,西方国家的政府债务(无论是中央政府层面的主权债务,还是地方政府层面的地方债),是源于没有未来收入去覆盖成本的社会福利、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庞大支出,并不是个别政府一时之间预期出错、决策不当造成的,而是这些社会福利、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本身就是蚕食租值、造成租值消散的恶法,最终到达坐食山空、爆发债务危机的境地是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了,完全不足为奇。但中国的地方债总体而言带来的是中国的经济腾飞、城市化进程一日千里,可见这种由地方政府来负责借债建设基础设施的政策是积累租值(财富)的良政,个别的失败个案不足为惧。自从中央政府打压房价、人为造成地方政府对卖地收入的预期出错之后,地方债才成为问题,也证明了非系统风险变成系统风险的根源出自中央政府。错误的政策总是这样人为增加风险——准确地说,是增加了地方政府正确预期土地的未来收入的信息费用。
从这篇文章,我想到以前我上过一门叫“中国经济”的课程,虽然那门课只有短短8学时,我还是在授课过程中对张五常教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的理解又有了新的领悟(那门课主要就是把《中国会否走向资本主义?》与《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内容简单地向学生介绍了一下)。当时我想着要把新领悟记下来写成文章,但一直没空。这次在《南都》发表关于中国地方债的文章,让我又想起教这门课时的新领悟,趁此机会赶紧写下来吧。
领悟之一,是我在向学生讲述《中国的经济制度》讲到中国的增值税本质是分成合约,增值税率全国统一就相当于县级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分成率是全国统一的,但这会违反了分成率要随土地质量的变化而变化(土地质量高的地方分成率也要高,因为分成率的本质是土地的价格)才能达成均衡的要求。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谈到分成合约时的一个注脚,却无意中破了案。马歇尔指出,如果地主、佃农都负担一部分土地的投资额,通过调整双方的投资额,可以使得统一的分成率也能达到有效率的均衡。张五常教授灵机一动,想到地价不就是企业(相当于佃农)所负担的土地的投资额吗?中国不同地方的地价是大不一样的,有些地方甚至是零地价、负地价地送地给企业,这些地方无一例外都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含义着土地的质量低下,本应收取较低的分成率,但在增值税率全国统一的前提下无法调整分成率,于是就用调整地价(减少佃农负担的土地投资额,甚至减到0或反过来补贴佃农以吸引他们也愿意来耕种特别劣质的土地)来达成均衡。
但为什么选择的是增值税率统一、地价不统一,而不是选择增值税率不统一、地价统一呢?《中国的经济制度》中提供的解释是一国之内有不同的税率不方便。但我上课讲到这里时,忽然觉得这个解释不够关键。为什么一国之内有不同税率就不方便了呢?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也有搞税收优惠的,就相当于是在调整税率。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税收优惠,一国之内是有不同税率的现象的呀。我再深入地思考,认为以下的解释能指出更关键的局限条件:增值税率是中央与地方之间谈判出来的(朱老时开始搞增值税,当时中央与地方之间有过多轮的博弈,来来去去反复改了很多次,才最终定下来),双方都是政府,不是市场上的主体,这谈判的结果不是市场竞争形成的。相比之下,地价是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谈判出来的,企业是市场上的主体,直接受到市场竞争的约束,它把这种竞争压力传递到地方政府,使得市场竞争的压力也约束着地方政府。也就是说,地价的形成包含着更充分的市场信息,是更能反映市场竞争的结果,所以让它变化,比起让增值税率变化,能更准确地传递市场信息。当然,同一个县里的每一块地的质量都各各不同,地价变化能更灵敏地反映土地质量的差别,比起为每一块地都调整增值税率,显然是交易费用低得多的选择。这也是原因之一,但我认为地价是地方政府与市场上的企业谈判出来、更直接地接触市场,才是最重要的原因。把决定如何使用土地的权力下放给县级政府,是因为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接近市场,了解市场的信息费用更低。同样的道理,让地价而非增值税率变动来传递市场信息,是因为参与地价谈判的主体之一就是直接在市场之内的企业,不要说中央政府、就连地方政府都不如它们了解市场的信息费用低。也就是说,虽然为了降低地役权谈判的交易费用而将决定如何使用土地的权力给了政府而不是市场,但在此大前提下,中国的土地使用制度的各项细节都安排成尽可能地接近市场,以最低的信息费用传递市场信息,确实是一个不世出的精妙制度啊!——更妙的是,如此连细节都精妙无比的制度,可并不是靠什么“顶层设计”搞出来的,而是在竞争着发展经济的压力下中央与地方政府通过多轮反复博弈而形成的。博弈的行为存在,博弈论这理论却是废物。博弈行为的意义是,正如市场上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一样,其实是一个传递、整合信息的过程(而不是像博弈论这废物理论那样把重心搞错成是利益不一致的参与博弈者只懂竞争、不肯合作)。通过多轮反复博弈,更接近市场的地方政府把各个局部的信息上传给中央,更能统观全局的中央政府整合所有信息不断调整制度的各个细节,最后臻于完美。
领悟之二,是增值税的设计使得地方政府以争取“增值税收入最大化”为目标。而在增值税率统一的情况下,增值税收入最大化就等同于“增值额最大化”。但增值额其实是什么呢?与学术意义上的增值额仅指企业的利润不同,增值税制度下的增值额是包含了工人的工资的,因为工资并不算入进项税额之中进行扣减。也就是说,这里的增值额是工人的工资加企业的利润。而所谓利润,其实是企业老板本人的工资与自有资本的利息,是老板兼任经营者(脑力劳动者)与出资人两种身份而要求获得的回报。撇开自有资金的利息不论,增值额实际上是参与企业生产经营的所有劳动者的工资,所以地方政府争取“增值额最大化”与企业老板争取利润最大化、工人争取工资收入(个人租值)最大化的目标是一致的,达成了管理学上最为推崇的“激励兼容”的美妙境界。
上课时讲到这里,我突然想到:最低工资法是人为地提高工人的工资,超过市场竞争所形成的均衡水平。上述的增值税制度下,地方政府会为了提高增值额而搞最低工资法去提高工人工资吗?这个问题在我脑海中一掠而过,但我一秒之间就已经找到答案:不会!因为这样偏离市场竞争的均衡去提高工人工资,并不能提高总的增值额,只会导致属于老板工资的企业利润被转移成工人工资。总的增值额是由市场竞争决定的,不会因为政府的人为扭曲而改变,最低工资法并不能提高增值额,只是改变了总的增值额在工人与老板之间的分配比例——严格来说,应该是改变了总的增值额在低质量劳动者(即其市场决定的均衡工资率低于最低工资法规定的人)与高质量劳动者(包括老板在内的高工资收入者)之间的分配比例。当然,高工资收入者会在自私的本性下保护自己的收入利益,高级员工会选择跳槽,老板会选择解雇不值得拿最低工资法所规定的那么高收入的低级员工。事实上偏离市场均衡,造成的不仅是不会提高总的增值额,反而会因为出现租值蚕食(低质量劳动者蚕食高质量劳动者的租值)而造成租值消散,总的增值额会是下降的,所以这对追求“增值额最大化”的地方政府是不利的。也就是说,地方政府要追求“增值额最大化”,唯一的办法是致力于提高落户于该地的企业的整体竞争力。整体竞争力上升,也就是企业的租值上升,增值额自然是跟着水涨船高。
领悟之三,是在“地区竞争制度”的约束下,中国的地方政府是不会搞“白象工程”(面子工程)的。以前右派愤青经常批评中国政府的一个常用“罪名”就是中国政府好大喜功、挥霍财政收入,把表面的市容市貌搞得光鲜漂亮,称之为“白象工程”。确实,在这种批评盛行的那个时候,外国的发展中国家有不少是经常搞“白象工程”的,把这种批评搬到中国身上来,似乎也顺理成章。但多年之后这种批评销声匿迹,我已经很久没再听见过了。这是因为事情发展了足够长的时间之后,事实证明中国的那些把市容市貌搞得光鲜漂亮的做法并没有像大量的发展中国家那样变成只是白花钱的“白象工程”,而是经济发展到配得上这样漂亮的城市景观。那些评论者也就无话可说了。
问题是这样的:花大钱把市容市貌搞得光鲜漂亮,最后可能是沦为“白象工程”(城市景观漂亮,但经济萧条,成了一个花架子空壳子),但也可能最终是漂亮的城市景观与繁荣的经济活动相得益彰。大量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前一种结果,中国却是普遍地出现后一种结果。但我们事前怎么能知道结果是哪一种呢?这并不需要“事后诸葛亮”。与企业类比一下就知道,任何商铺在开张之前都要好好地装修一番,店面光鲜漂亮才能吸引顾客光临。这光鲜漂亮是招徕生意的前期投资,可不是打肿脸充胖子的无谓炫耀——这正是中国美化城市与大量的发展中国家“白象工程”之间的本质区别!中国的地方政府花大钱把市容市貌搞得光鲜漂亮,是为了接下来招商引资作的铺垫,是“筑巢引凤”,花出去的钱在未来是有回报的,只要预期正确,结果当然是经济繁荣与漂亮的城市景观相得益彰。如果一个地方政府只为了面子好看而搞“白象工程”,钱花出去之后就已经心满意足,后续不会搞招商引资,那自然是没有经济繁荣随后而来,正如商铺光装修不开门迎客,怎么会有其后的生意兴隆呢?当然不排除有个别城市决策失当、预期错误,把城市搞得光鲜漂亮之后,虽然跟着也努力招商引资了,却不甚成功(所谓的“鬼城”,其实中国大部分被称“鬼城”的新城区并不真的是鬼城,只是建成的时间还短而已),正如不是所有商铺装修好之后开门迎客就一定生意兴隆的。但这是个别城市的失策,是非系统风险,总的来说中国的城市大多都在装修一新后客似云来,相当成功,没有系统风险,说明这个“先装修,后引商”的策略整体而言是非常正确的。——大家注意到了吗?这一段分析与一开头提到的发表于《南都》的文章分析中国的地方债与西方国家各个层级的政府债务有本质的区别,是类似的逻辑。我写那篇文章而引起对这门课的新领悟的回忆,就是这个缘故。
但是,这个“装修城市以便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现象还可以作更深入的分析。为什么中国的地方政府会选择“装修城市”而不是搞“白象工程”呢?关键在于地方政府美化城市的钱是自己出的!要是有一个地方政府只是为了面子好看而美化城市,如前所述,在这样的动机之下,其后是不会有招商引资之举的,这笔钱花了之后便“然后就没然后”了,是白花了的。接下来还要再美化城市,就没钱了。相比之下,如果一个地方政府是为了招商引资而先装修城市,经济发展随后而来,前面花的钱其实是投资,是有未来收入作为回报的,钱花了之后带来更多的钱,这个地方政府就有更多的钱把城市装修得更漂亮,又进一步招徕更多更高级的企业,带来更多的钱……如此良性循环,地方政府就会一直有钱花在美化城市上,不会像搞“白象工程”的地方那样只有第一次的投入。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搞的是“白象工程”而不是装修招商,往往是因为钱来自于中央政府,而不是地方政府自己负担,以一国之财富去支撑一个城市的挥霍,蚕食租值可以挺住一段时间,但没有中国城市那样“钱生钱”的投资回报的良性循环,迟早是坐食山空的下场。
像今年韩国的冬季奥运会在平昌举行,那是一个在此之前主要靠种植土豆为支柱性产业、连韩国人也没几个听说过的穷乡僻壤,靠着把冬奥会放在那里硬给它建了那么多现代化的城市设施,但那种冰天雪地的地方怎么适合发展现代经济?我认为平昌在冬奥会结束后是没有未来的,又是一个“白象工程”而已。它不是平昌自己申请要办冬奥会的,建场馆的钱也不是它自己负担的,这种来自于中央政府资助的“突击建设”,不是弗里德曼所说的“永久性收入”,对于长远的经济增长是没有真正的拉动刺激之力的。相比之下,广州举办亚运会使得广州的市容市貌焕然一新,形成新的城市中轴线,却是大有好处的(但亚运村的楼价上涨乏力,反映着那个地方在客观上就是没能成为经济发展新中心,不以政府在那里花了大钱为转移)。一来广州本身自古以来就是珠三角的经济中心,二来亚运会的建设资金主要是广州自己负担的,受到未来要有足够的投资回报的约束。
上这门课时,雄安的新闻还没出来。就在这门课上完没多久,雄安的新闻就出来了。我当时听了就在心里暗暗一笑,觉得简直就像是我刚好提前“预言”一样。雄安的未来如何?只要看到它的建设不是由当地的地方政府自己出资,而是中央政府越俎代庖,就该知道了。
不过后来我再深入思量,觉得雄安这事很可能只是北京出钱养起河北来解决环保问题的一个载体。我以前写过关于“北京-河北环保问题”的文章,指出北京的户籍福利偏高造成京冀经济发达程度差异巨大,河北愿意承受污染的代价发展经济,北京却不愿意,于是造成严重的矛盾。治本之道当然是废除北京的偏高的户籍福利,但一来政治上难以做到,二来“远水救不了近火”,一个简单易行的治标之法是由北京出钱养起河北,出的钱多到河北愿意放弃搞污染工业来发展经济,相当于是把“污染权”买过来了。但直接这样给钱也是在政治上难以做到,于是就找一个特别花钱的项目作为北京出钱向河北购买“污染权”的载体——这,就是雄安!雄安建设的表面理由是要分担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但既然要做“副首都”,应该选择一个与北京之间交通便利之处,却故意选雄安这么一个所有交通设施都要从头建起的地方,大大地增加成本,岂不大谬?但如果理解为是要做北京给河北出钱购买“污染权”的载体,那当然不能是“浅碟子”,稍微多花点钱就满了的话,怎么买得下要能养起整个河北心甘情愿放弃发展工业的昂贵的“污染权”?
这就是我对雄安的“猜想”,不知大家以为然否?这猜想的验证,就让我们拭目以待未来吧!